清明前后的北京,风里总飘着些槐花香和烧纸的余味。常有人攥着皱巴巴的纸条问路口的交警:“万安公墓怎么走?”不是手机导航不好用,是他们想确认——那片埋着父母、祖父母,或者某个读过的作家的土地,究竟藏在京城的哪一角,是不是还像记忆里那样,有遮天的国槐和飘着月季香的小路。
万安公墓的具体位置,在海淀区香山南路万安里1号。说起来也巧,它刚好卡在“城市”和“山野”的缝儿里:往西望是西山余脉的浅黛色山影,像幅没画完的水墨画;往东走两三百米,就是昆玉河的支流,春天的时候,河边的柳树会把枝条垂进水里,晃得碎银子似的波光;北边隔着一条篱笆墙,是北京植物园的侧门,有时候能听见园子里游客的笑声飘过来;南边过了火器营桥,就是车水马龙的蓝靛厂中路——可只要一进万安的门,那些喧嚣就像被门楣上的烫金字体挡住了,柏油路两旁的国槐漏下细碎的阳光,连风都慢了半拍,像怕惊着什么。
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建园时,选址的人就动了心思。他们说这儿“背山面水,藏风聚气”,是块“吉地”。可在老北京人眼里,哪儿有那么多讲究?不过是“离城不远,又能沾点西山的野趣”。当年住在蓝靛厂的老人们回忆,民国时候去万安上坟,骑辆自行车就行,沿着香山南路往北,过了第三个卖茶水的摊子,就能看见那座墨绿色的门楣,上面“万安公墓”四个烫金大字,还是当年书法家沈尹默写的,笔锋里带着点瘦金体的清劲,这么多年没换过。
再说起万安的位置,哪是一个地址能装下的?它是朱自清先生墓前的那棵银杏——从正门进去,沿着银杏道走到底,右转第三排,墓碑上刻着“朱自清先生之墓”,旁边的银杏每年秋天都落满金黄的叶子,像给先生铺了层书笺;是戴望舒墓旁的老松树——在东边的松林区,树龄比公墓还大,枝桠像张开的手,刚好罩住刻着“戴望舒”的石碑,有人说“这树是在替诗人守着雨巷的回忆”;更是普通人的故事:去年有个扎马尾的姑娘,攥着妈妈给的纸条找外婆的墓,纸条上写着“月季园第三排左数第五个”。她进园没走几步,就闻见浓郁的月季香,顺着香味拐过两座凉亭,果然看见一排墓碑前摆着月季,最中间的那块,刻着“陈淑兰”三个字,底下还有行小字“爱月季,爱家人”。姑娘蹲下来,把带来的枣泥饼放在碑前,轻声说:“外婆,我妈让我带了你最爱的稻香村。”风刚好吹过来,把饼香吹向西山的方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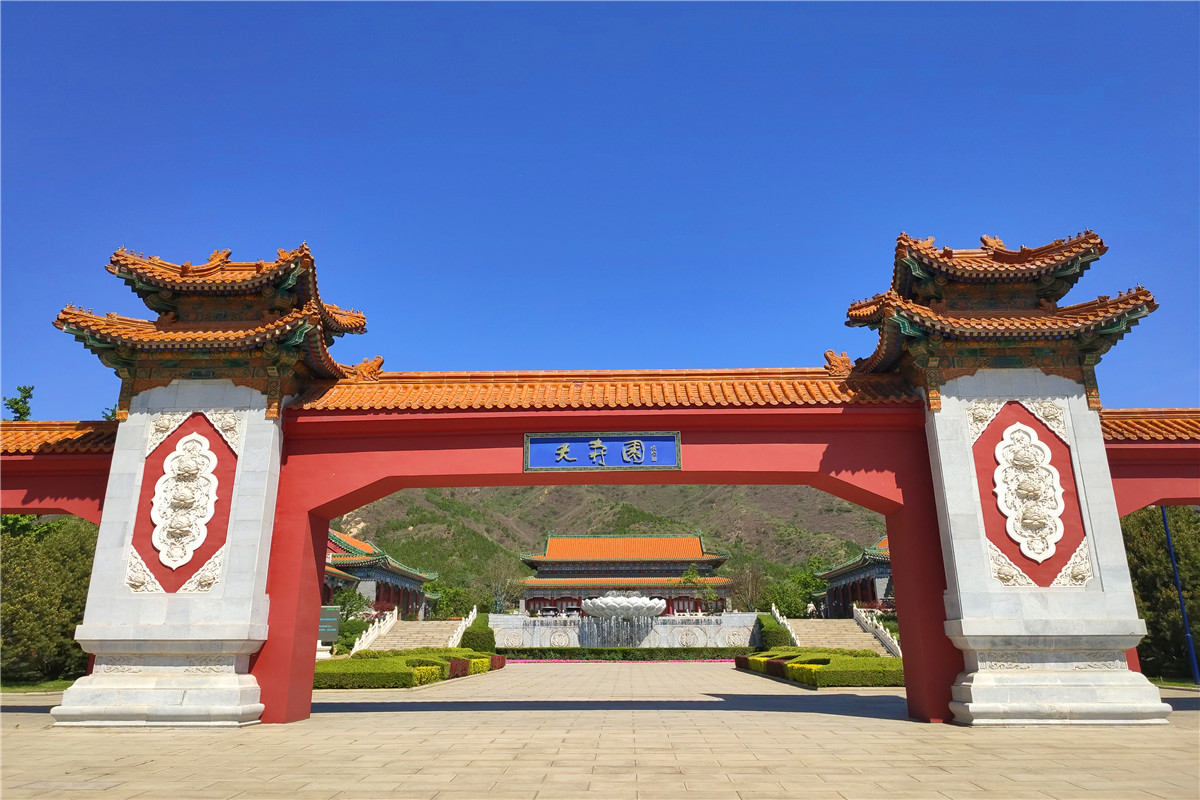
有人说,万安公墓的位置是“活”的。它不是地图上的东经116.28度、北纬39.95度,是“从家里出发,坐360路公交到万安站,下车往南走50米,看见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就是”的熟门熟路;是“每年清明带一束白菊,沿着柏油路走,总能遇见当年一起给父亲上坟的老邻居”的亲切;是“站在墓碑前,能听见西山的风穿过树林,像母亲当年喊你回家吃饭的声音”的温暖。

那天傍晚,我在万安门口遇见个坐轮椅的老人。他让护工推着他往门里望,说:“我年轻的时候,总陪我爸来这儿看我爷爷。那时候门口有个卖糖瓜的摊子,我爸每次都买两块,给我一块,给爷爷的墓碑前放一块。现在摊子没了,可那股糖瓜的甜味儿,还在风里飘着呢。”护工问:“爷爷的墓在哪儿?”老人笑了:“在松林区的第三排,旁边有棵老松树——不用找,我闭着眼都能走过去。”
原来万安公墓的位置,从来不是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