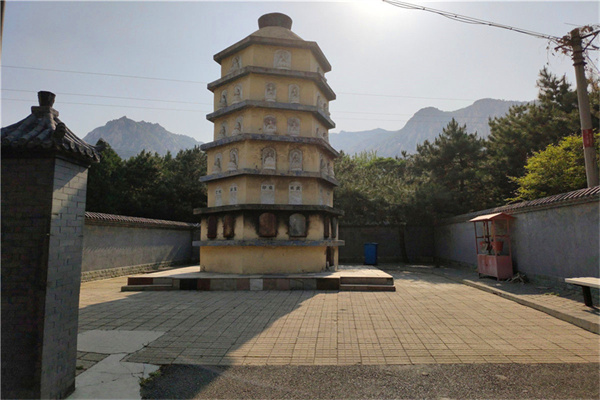秋天的风裹着槐叶的碎香,我陪楼下的李婶去天慈墓园看她故去的老伴儿。清晨6点半的地铁14号线张郭庄站A口,晨雾还没散透,就看见那辆蓝白相间的中巴车——车身上“天慈墓园便民线”的红字被路灯映得暖融融的,司机老周正蹲在车头擦后视镜,见我们过来,抬头笑:“婶儿又来啦?先把手里的纸扎放车厢里,我留了后排宽点儿的位置。
这趟连接地铁口与墓园的班车,像根细细的线,串起了北京城西许多家庭的牵挂。工作日的话,每天有四班车:早6:50是第一班,载着晨练刚结束的老人;8:30那班多是赶在上班前请假的年轻人;10:10的车里常能看见拎着新鲜菊花的阿姨;最晚的13:00班,大多是刚下班的上班族,抱着电脑包坐在座位上补觉。到了周末或清明、寒衣节这样的日子,会加开两班早6:30和9:00的车——老周说,去年清明他拉过一对年轻夫妻,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,妈妈把孩子的小手套塞在墓碑缝里,说“爷爷看,宝宝会抓东西了”,那班车的车厢里,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。

坐过几趟就摸出了规律:想占个能放祭品的位置,得提前10分钟到;周末人多的时候,常有人把折叠椅放在过道里,却从不会有人抱怨——毕竟都是去看亲人的,递一瓶矿泉水的功夫,就能聊起“我家老头儿生前爱喝二锅头”“我妈去年还在这儿种了棵月季”。老周的车里总备着一箱矿泉水,是墓园给乘客留的,瓶身贴着手写的便签:“路上渴了喝,别忘带身份证登记。”他说上个月有个姑娘急着赶车,把包落在位子上,里面有她爸爸的老照片,他追出两站地才追上——“那照片比啥都金贵”。
返程的时间也得记准:墓园那边的发车点就在正门口的梧桐树下,工作日是8:00、9:40、11:20、14:00,周末加10:00和12:30。有次我坐11:20的返程车,遇见个穿墨绿旗袍的老太太,抱着个陶瓷罐儿,说那是她老伴儿生前养的君子兰,“他走了我养不好,送这儿来陪他”。车上的人都安静着,直到车开上莲石路,有人轻声说“看,那边的银杏黄了”,老太太望着窗外,伸手摸了摸怀里的罐子,像摸着老伴儿的手背。

其实这趟车最动人的,从来不是精准的时刻表。是老周看见拎重东西的人,会主动搭把手搬上车;是乘客之间互相递纸巾时的沉默;是有人迟到跑过来,全车人等着他的那两分钟——没有催促,只有司机说“慢点儿,别摔着”。上星期我自己坐这班车,邻座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,抱着束白百合,车开了半小时才小声说:“我爸走的时候我在外地,没见着最后一面。”前排的阿姨听见了,把自己手里的桂花糕递过去一块:“吃口热的,你爸要是看见,得怪你不吃早饭。”
昨天再去坐班车,发现车门上多了张新贴的通知:“下周一起,早班发车时间提前10分钟,因莲石路修路,请乘客提前15分钟到站。”下面附了墓园的公众号二维码,备注着“实时查路况,别跑空”。老周擦着方向盘说:“昨天有个姑娘打了三回电话问时间,怕赶不上给妈妈烧纸,我跟她说‘放心,我等你’——其实我们这班车,等的不是人,是心里那口气儿。”
车窗外的树影掠过,我看见李婶摸着墓碑上的照片,轻声说:“老头儿,今儿坐老周的车来的,他还问你咋没跟我一块儿下棋。”风卷着她的白发,吹过